1 坦克碾人肠胃不好者误入【六四王维林只身挡坦克录像下载:一人敌一国的勇气】 周四 五月 19, 2011 6:11 am
坦克碾人肠胃不好者误入【六四王维林只身挡坦克录像下载:一人敌一国的勇气】 周四 五月 19, 2011 6:11 am
Admin
Admin
http://www.zonghexinwen.net/newsimg/20090914/200909140017_flv8674722083926d50325fc4032a82b03f7218a11dc001.flv】不能正常下载请复制地址到下载框  【图片集】:http://www.guardian.co.uk/world/gallery/2009/jun/05/tiananmen-square-protests-1989-china#/?picture=348436701&index=13
【图片集】:http://www.guardian.co.uk/world/gallery/2009/jun/05/tiananmen-square-protests-1989-china#/?picture=348436701&index=13

 只身挡坦克的王维林。
只身挡坦克的王维林。
前不久,美国之音记者舒国符约我做一个摄影和录音相结合的采访,原因是美国伯克利大学的一个人类学教授提供了一份最新研究结果,希望我对他的研究结果作一评论。这位教授断定王维林在挡坦克的现场先是落入便衣警察手中,然后又落入戒严部队军人手中,凶多吉少。
这位人类学教授是研究人类肢体语言(肢体动作)的专家。多年来,他一直关注王维林的命运,反覆研究有关王维林挡坦克,以及最终被人推走的那一段录像。有关的录像不止一份,但大同小异,是不同的外国记者在北京饭店的阳台上拍摄的,时间,地点,拍摄角度都是一样的。
王维林挡坦克的时间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地点在东长安街,靠近天安门广场。从录像上看,王维林挡住十多辆沿着东长安街由东往西驶向天安门
广场的坦克。数次左右来回挡住试图绕过去的坦克车队,并一度爬上第一辆坦克,向坦克里的军人喊话。先有一名骑自行车的青年上来靠近王维林,与王维林简短交
谈,紧接着又上来两名青年,拉走王维林,随即一左一右挟持王维林离开现场,快速到了路边。 多年来,不少人认为将王维林拉走的三个青年是好心的民众,而到了路旁的王维林趁机躲入路旁的人群中,安全地消失了。
这位人类学教授在仔细研究了三名青年和王维林的肢体语言后认为,这三位青年不是普通的民众,而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便衣人员。王维林没有安全脱走,而是当场被捕了,并且凶多吉少,因此至今下落不明。
出于多年来对王维林的关心,也为了发表评论,我再次反覆观看了相关的录像,使用的是大屏幕,而且可以随意控制播放速度,看的非常仔细,并十
分注意三位青年和王维林的肢体语言。如果不是这位人类学教授的提示,一般人不会太注意肢体语言,当时也没有类似于冲突的,过激的肢体冲突。两位后来出现的
青年非常专业地一左一右地挟持住王维林,仔细观察会发现扭胳膊和顶住后背关节处的动作(我考入北大时是武警的职业军官,多少了解这些使人瘫软的手段),原
先以死抗争的王维林似乎想抵抗也使不出劲,只能被动地朝路旁走去。先出现的青年在王维林开始被挟持着离开道路中央的时候,立即对着坦克打手势,人类学教授
认为,这不是普通人毫无章法的肢体动作,而是经过专业训练,富有确定含义的手势。 我细心观看多遍,越来越确信人类学教授的专业判断。对我而言,尤其重要的是,这位教授所选择的录像,比过去所常见的录像带多了十几秒时
间,一直延续到王维林被推上人行道,我注意到那里只有零星一两个身份不明的便衣人员,根本就没有围观的人群,王维林无处可躲。更重要的是,那里已经停着一
排排的坦克,说明那里不是戒严部队的警戒区,也是接近警戒区的地点,距离天安门广场非常近,就在南池子附近,根本不会允许民众靠近。六月四日凌晨至上午,
就是在这个区域,大批民众试图进入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一次次被戒严部队军人开枪击倒,这里的惨烈境况仅次于西长安街。我在<天安门血腥清
场>一书中引用多位目击者的证词,对南池子的屠杀有具体的记录。 过去,我一直以为王维林挡坦克的地点接近北京饭店,距离天安门广场较远,相信那里的路旁会有许多民众,王维林到了路旁,可以迅速没入人群,安全离开。
我努力使用控制器,不断地倒带停带,终于看清了坦克侧面的编号,知道这些坦克属于天津警备区坦克1师。
如果上述人类学教授的研究结果和我的评论和判断无误,基本可以断定,王维林凶多吉少,可能已经在戒严部队军人的暴力下遇难。天安门广场清场
前后在广场内外被捕的学生和民众都遭到军人的暴打,用木棒,用枪托,打死不少人,受伤致残的更多。山西的大学生高旭在广场被捕,被打伤致残,他叙述了具体
的经历。被捕者都关押在天安门城楼左右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里,那里成了军人泄愤的大刑场。被捕者三天没有吃喝。 我自始至终认为“王维林”这个名字不是独身挡坦克的青年的真实姓名,人们都这样传说而已。从他的穿着打扮,应该是一个学生,但不是北京的学生,他在挡坦克的过程中,随身带着一个小包,只有外地的学生才会带着小包,放一些牙膏牙刷之类的日用品和学生证等证件。
人类学教授的研究结果和我的评论,可能已经放在美国之音的网址上,应该是带视频的,有心深入了解的朋友可以去搜寻一下。 每当谈到“六四”,人们想到的第一位英雄,就是在北京长安街上只身挡坦克的王维林。王维林是谁?他还活着吗?
每当谈到“六四”,人们想到的第一位英雄,就是在北京长安街上只身挡坦克的王维林。王维林是谁?他还活着吗?
原89民运学生领袖、《六四档案》网站主编封从德,近日就人们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封从德表示,他和大家一样,并不确切知道王维林是谁,他只相信大多数人的说法,王维林是一位青年工人。封从德认为,王维林是工人还是学生,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王维林挡坦克的照片,象征着20世纪发生在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事件,他说: [/size]“王维林挡坦克的照片,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一幅画面,一个象征。就是这个画 面,象征了肆虐半个地球、整个20世纪的共产政权,走向衰亡。它灭亡的起点,就是‘六四’。而‘六四’真正的象征,就是王维林。”
王维林6月4日 第二天,在北京东长安街天安门广场附近,挡坦克的照片和录像,是美国记者,当时从北京饭店楼上使用长焦距镜头拍摄。美国《时代周刊》把王维林列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位人物”。
关心王维林下落的,不仅仅是全世界的华人,包括美国前总统布什、美国知名记者华莱士,都亲自向中国领导人询问王维林的下落。封从德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王维林已经成为一个“神话”。
根据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一位名叫约瑟夫的人类行为学家,从王维林挡坦克的完整录像分析,王维林后来被人带走。
这位人类学教授是研究人类肢体语言(肢体动作)的专家。多年来,他一直关注王维林的命运,反覆研究有关王维林挡坦克,以及最终被人推走的那一段录像。有关的录像不止一份,但大同小异,是不同的外国记者在北京饭店的阳台上拍摄的,时间,地点,拍摄角度都是一样的。
王维林挡坦克的时间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地点在东长安街,靠近天安门广场。从录像上
看,王维林挡住十多辆沿着东长安街由东往西驶向天安门广场的坦克。数次左右来回挡住试图绕过去的坦克车队,并一度爬上第一辆坦克,向坦克里的军人喊话。先
有一名骑自行车的青年上来靠近王维林,与王维林简短交谈,紧接着又上来两名青年,拉走王维林,随即一左一右挟持王维林离开现场,快速到了路边。
多年来,不少人认为将王维林拉走的三个青年是好心的民众,而到了路旁的王维林趁机躲入路旁的人群中,安全地消失了。
这位人类学教授在仔细研究了三名青年和王维林的肢体语言后认为,这三位青年不是普通的民众,而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便衣人员。王维林没有安全脱走,而是当场被捕了,并且凶多吉少,因此至今下落不明。
出于多年来对王维林的关心,也为了发表评论,他再次反覆观看了相关的录像,使用的是大
屏幕,而且可以随意控制播放速度,看的非常仔细,并十分注意三位青年和王维林的肢体语言。如果不是这位人类学教授的提示,一般人不会太注意肢体语言,当时
也没有类似于冲突的,过激的肢体冲突。两位后来出现的青年非常专业地一左一右地挟持住王维林,仔细观察会发现扭胳膊和顶住后背关节处的动作,原先以死抗争
的王维林似乎想抵抗也使不出劲,只能被动地朝路旁走去。先出现的青年在王维林开始被挟持着离开道路中央的时候,立即对着坦克打手势,人类学教授认为,这不
是普通人毫无章法的肢体动作,而是经过专业训练,富有确定含义的手势。
他细心观看多遍,越来越确信他的专业判断。对他而言,尤其重要的是,这位教授所选择的
录像,比过去所常见的录像带多了十几秒时间,一直延续到王维林被推上人行道,注意到那里只有零星一两个身份不明的便衣人员,根本就没有围观的人群,王维林
无处可躲。更重要的是,那里已经停着一排排的坦克,说明那里不是戒严部队的警戒区,也是接近警戒区的地点,距离天安门广场非常近,就在南池子附近,根本不
会允许民众靠近。六月四日凌晨至上午,就是在这个区域,大批民众试图进入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一次次被戒严部队军人开枪击倒,这里的惨烈境况仅次于西长安
街。在<天安门血腥清场>一书中引用多位目击者的证词,对南池子的屠杀有具体的记录。
过去,他一直以为王维林挡坦克的地点接近北京饭店,距离天安门广场较远,相信那里的路旁会有许多民众,王维林到了路旁,可以迅速没入人群,安全离开。
他努力使用控制器,不断地倒带停带,终于看清了坦克侧面的编号,知道这些坦克属于天津警备区坦克1师。
如果上述人类学教授的研究结果和判断,基本可以断定,王维林凶多吉少,可能已经在戒严
部队军人的暴力下遇难。天安门广场清场前后在广场内外被捕的学生和民众都遭到军人的暴打,用木棒,用枪托,打死不少人,受伤致残的更多。山西的大学生高旭
在广场被捕,被打伤致残,他叙述了具体的经历。被捕者都关押在天安门城楼左右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里,那里成了军人泄愤的大刑场。被捕者三天没有吃
喝。
[size=12]以后如果有一个人说他是王维林,可能大家都很难相信。‘六四’实际上最后成为一个宗教
性事件,每年‘六四’对死者的纪念,已经成为一个宗教仪式。我们都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去悼念死者,而王维林成为一个‘神话’。王维林作为“六四”的象征,永
远活着。王维林和许多“六四”英雄一样,已经遇难。

丁子霖所搜寻的「六四受难者名册」中,这些名字仍然像黑色纪念碑一样沉重:
六部口才是真正坦克辗人的地方
节录自
高新《六三之夜:谁开枪?》
我
们在天安门万余名大学生和市民群众面临生命危险,同时也不愿由于天安门的抵抗给士兵造成生命损失的时候,理智地选择了妥协与和平,包围天安门广场的部队在
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和平主张的前提下应该说表现的是比较理智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负责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的部队主要不是从西线开枪打进来、已经失去理
智的部队,而是从人民大会堂等处出来的。没有遭到过抵抗的部队当然也就没有开过枪的部队。但是,长安街上的戒严部队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和平主张而全部理智起
来。当从天安门广场撤出来的大学生和市民陆续到达六部口地区时,一些惨无人道的士兵竟开枪扫射并驾着坦克冲向最多向它们扔了几块石头的人群。我和程真、沙
涛因最后撤离,所以幸免在六部口遭难。当我们三人手拉手步行到六部口以南的音乐堂时,一群刚被打回来的市民劝我们﹕“学生,再不能往前走了,前面的大兵一见你们这样打扮的就开枪。”我让程真和沙涛摘下头上的写有“绝食”字样的布条,我摘下胸前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徽,三个人还是硬着头皮朝六部口走去。
到达时,我们正好见到最后两具尸体被抬上一辆北京一三○卡
车。这辆车是被我和程真在前门箭楼东侧劝住运伤员的。当时,这辆车打着一面白底红十字旗对着驶近的坦克朝天安门广场里面冲,我们劝阻时程真险些被辗在车轮
下面。六部口的群众告诉我们,在我们到达这里之前已经运走了一批尸体,连坦克辗加机枪扫一共死了十三个人。事后有目击者告诉我是十一个人。横穿过长安街
后,我和程真、沙涛坐在六部口十字路口的西北角休息。最近的一辆坦克离我们不足两米,但这时它们已不再杀人了。也可能我们不骂它们法西斯的缘故。
从监狱里出来后我了解到,六部口遭难的十余人里,尚有一个坦克履带下的幸存者。他是北京某公司的职员,六月四号早上他听到中共开枪镇压的消息从家里出来,刚到六部口就遇上了撤出的学生队伍。他告诉我﹕“当时坦克驶近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朝人群里辗,所以也没有赶紧躲避的思想准备。从坦克开到我脸前的那一刻,我就甚么也不知道了。三天以后,我在医院里醒过来,医生都不敢看我。”他的右胳膊从肩膀处永远没有了,身上落下七十六处伤。刚被坦克碾过后头皮和一只耳朵被撕开,惨不忍睹。他在住院治疗期间,一位“同情者”诱骗后又拋弃了他的未婚妻,这个可怜的姑娘因为深感负疚和愧悔而自尽身亡。临死前留下遗书,请求他的宽恕并希望他能为自己料理后事。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坦克履带下的唯一幸存者时,正好是他刚从原来未婚妻的追悼会上回来。
写到这里,我想再补一句题外话﹕国内的假肢厂工人能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潜入工厂为这位坦克履带下的幸存者免费制作假肢,逃出国的一些“天安门勇士”(当然不是全部)在挥霍捐款时想到过“六四”的死难者和尚留在国内的受难者吗﹖不要忘了,当时,许许多多的大学生和北京市民都是受了我们的宣传上街,为了保护我们在天安门坚持民主斗争的大学生们才去堵截军车,才饮弹身亡或留下终生残疾的。 (左)坦克压扁了一辆电单车(右)一名体育学院的学生 ,被坦克辗断了双腿的情况
(左)坦克压扁了一辆电单车(右)一名体育学院的学生 ,被坦克辗断了双腿的情况



由
1989年至1999年期间,
丁子霖教授共收集了受难者者共155人,
按此参阅按此进入)
:]
 【图片集】:http://www.guardian.co.uk/world/gallery/2009/jun/05/tiananmen-square-protests-1989-china#/?picture=348436701&index=13
【图片集】:http://www.guardian.co.uk/world/gallery/2009/jun/05/tiananmen-square-protests-1989-china#/?picture=348436701&index=13
 只身挡坦克的王维林。
只身挡坦克的王维林。前不久,美国之音记者舒国符约我做一个摄影和录音相结合的采访,原因是美国伯克利大学的一个人类学教授提供了一份最新研究结果,希望我对他的研究结果作一评论。这位教授断定王维林在挡坦克的现场先是落入便衣警察手中,然后又落入戒严部队军人手中,凶多吉少。
这位人类学教授是研究人类肢体语言(肢体动作)的专家。多年来,他一直关注王维林的命运,反覆研究有关王维林挡坦克,以及最终被人推走的那一段录像。有关的录像不止一份,但大同小异,是不同的外国记者在北京饭店的阳台上拍摄的,时间,地点,拍摄角度都是一样的。
王维林挡坦克的时间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地点在东长安街,靠近天安门广场。从录像上看,王维林挡住十多辆沿着东长安街由东往西驶向天安门
广场的坦克。数次左右来回挡住试图绕过去的坦克车队,并一度爬上第一辆坦克,向坦克里的军人喊话。先有一名骑自行车的青年上来靠近王维林,与王维林简短交
谈,紧接着又上来两名青年,拉走王维林,随即一左一右挟持王维林离开现场,快速到了路边。 多年来,不少人认为将王维林拉走的三个青年是好心的民众,而到了路旁的王维林趁机躲入路旁的人群中,安全地消失了。
这位人类学教授在仔细研究了三名青年和王维林的肢体语言后认为,这三位青年不是普通的民众,而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便衣人员。王维林没有安全脱走,而是当场被捕了,并且凶多吉少,因此至今下落不明。
出于多年来对王维林的关心,也为了发表评论,我再次反覆观看了相关的录像,使用的是大屏幕,而且可以随意控制播放速度,看的非常仔细,并十
分注意三位青年和王维林的肢体语言。如果不是这位人类学教授的提示,一般人不会太注意肢体语言,当时也没有类似于冲突的,过激的肢体冲突。两位后来出现的
青年非常专业地一左一右地挟持住王维林,仔细观察会发现扭胳膊和顶住后背关节处的动作(我考入北大时是武警的职业军官,多少了解这些使人瘫软的手段),原
先以死抗争的王维林似乎想抵抗也使不出劲,只能被动地朝路旁走去。先出现的青年在王维林开始被挟持着离开道路中央的时候,立即对着坦克打手势,人类学教授
认为,这不是普通人毫无章法的肢体动作,而是经过专业训练,富有确定含义的手势。 我细心观看多遍,越来越确信人类学教授的专业判断。对我而言,尤其重要的是,这位教授所选择的录像,比过去所常见的录像带多了十几秒时
间,一直延续到王维林被推上人行道,我注意到那里只有零星一两个身份不明的便衣人员,根本就没有围观的人群,王维林无处可躲。更重要的是,那里已经停着一
排排的坦克,说明那里不是戒严部队的警戒区,也是接近警戒区的地点,距离天安门广场非常近,就在南池子附近,根本不会允许民众靠近。六月四日凌晨至上午,
就是在这个区域,大批民众试图进入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一次次被戒严部队军人开枪击倒,这里的惨烈境况仅次于西长安街。我在<天安门血腥清
场>一书中引用多位目击者的证词,对南池子的屠杀有具体的记录。 过去,我一直以为王维林挡坦克的地点接近北京饭店,距离天安门广场较远,相信那里的路旁会有许多民众,王维林到了路旁,可以迅速没入人群,安全离开。
我努力使用控制器,不断地倒带停带,终于看清了坦克侧面的编号,知道这些坦克属于天津警备区坦克1师。
如果上述人类学教授的研究结果和我的评论和判断无误,基本可以断定,王维林凶多吉少,可能已经在戒严部队军人的暴力下遇难。天安门广场清场
前后在广场内外被捕的学生和民众都遭到军人的暴打,用木棒,用枪托,打死不少人,受伤致残的更多。山西的大学生高旭在广场被捕,被打伤致残,他叙述了具体
的经历。被捕者都关押在天安门城楼左右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里,那里成了军人泄愤的大刑场。被捕者三天没有吃喝。 我自始至终认为“王维林”这个名字不是独身挡坦克的青年的真实姓名,人们都这样传说而已。从他的穿着打扮,应该是一个学生,但不是北京的学生,他在挡坦克的过程中,随身带着一个小包,只有外地的学生才会带着小包,放一些牙膏牙刷之类的日用品和学生证等证件。
人类学教授的研究结果和我的评论,可能已经放在美国之音的网址上,应该是带视频的,有心深入了解的朋友可以去搜寻一下。
 每当谈到“六四”,人们想到的第一位英雄,就是在北京长安街上只身挡坦克的王维林。王维林是谁?他还活着吗?
每当谈到“六四”,人们想到的第一位英雄,就是在北京长安街上只身挡坦克的王维林。王维林是谁?他还活着吗?原89民运学生领袖、《六四档案》网站主编封从德,近日就人们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封从德表示,他和大家一样,并不确切知道王维林是谁,他只相信大多数人的说法,王维林是一位青年工人。封从德认为,王维林是工人还是学生,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王维林挡坦克的照片,象征着20世纪发生在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事件,他说: [/size]“王维林挡坦克的照片,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一幅画面,一个象征。就是这个画 面,象征了肆虐半个地球、整个20世纪的共产政权,走向衰亡。它灭亡的起点,就是‘六四’。而‘六四’真正的象征,就是王维林。”
王维林6月4日 第二天,在北京东长安街天安门广场附近,挡坦克的照片和录像,是美国记者,当时从北京饭店楼上使用长焦距镜头拍摄。美国《时代周刊》把王维林列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位人物”。
关心王维林下落的,不仅仅是全世界的华人,包括美国前总统布什、美国知名记者华莱士,都亲自向中国领导人询问王维林的下落。封从德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王维林已经成为一个“神话”。
根据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一位名叫约瑟夫的人类行为学家,从王维林挡坦克的完整录像分析,王维林后来被人带走。
这位人类学教授是研究人类肢体语言(肢体动作)的专家。多年来,他一直关注王维林的命运,反覆研究有关王维林挡坦克,以及最终被人推走的那一段录像。有关的录像不止一份,但大同小异,是不同的外国记者在北京饭店的阳台上拍摄的,时间,地点,拍摄角度都是一样的。
王维林挡坦克的时间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地点在东长安街,靠近天安门广场。从录像上
看,王维林挡住十多辆沿着东长安街由东往西驶向天安门广场的坦克。数次左右来回挡住试图绕过去的坦克车队,并一度爬上第一辆坦克,向坦克里的军人喊话。先
有一名骑自行车的青年上来靠近王维林,与王维林简短交谈,紧接着又上来两名青年,拉走王维林,随即一左一右挟持王维林离开现场,快速到了路边。
多年来,不少人认为将王维林拉走的三个青年是好心的民众,而到了路旁的王维林趁机躲入路旁的人群中,安全地消失了。
这位人类学教授在仔细研究了三名青年和王维林的肢体语言后认为,这三位青年不是普通的民众,而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便衣人员。王维林没有安全脱走,而是当场被捕了,并且凶多吉少,因此至今下落不明。
出于多年来对王维林的关心,也为了发表评论,他再次反覆观看了相关的录像,使用的是大
屏幕,而且可以随意控制播放速度,看的非常仔细,并十分注意三位青年和王维林的肢体语言。如果不是这位人类学教授的提示,一般人不会太注意肢体语言,当时
也没有类似于冲突的,过激的肢体冲突。两位后来出现的青年非常专业地一左一右地挟持住王维林,仔细观察会发现扭胳膊和顶住后背关节处的动作,原先以死抗争
的王维林似乎想抵抗也使不出劲,只能被动地朝路旁走去。先出现的青年在王维林开始被挟持着离开道路中央的时候,立即对着坦克打手势,人类学教授认为,这不
是普通人毫无章法的肢体动作,而是经过专业训练,富有确定含义的手势。
他细心观看多遍,越来越确信他的专业判断。对他而言,尤其重要的是,这位教授所选择的
录像,比过去所常见的录像带多了十几秒时间,一直延续到王维林被推上人行道,注意到那里只有零星一两个身份不明的便衣人员,根本就没有围观的人群,王维林
无处可躲。更重要的是,那里已经停着一排排的坦克,说明那里不是戒严部队的警戒区,也是接近警戒区的地点,距离天安门广场非常近,就在南池子附近,根本不
会允许民众靠近。六月四日凌晨至上午,就是在这个区域,大批民众试图进入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一次次被戒严部队军人开枪击倒,这里的惨烈境况仅次于西长安
街。在<天安门血腥清场>一书中引用多位目击者的证词,对南池子的屠杀有具体的记录。
过去,他一直以为王维林挡坦克的地点接近北京饭店,距离天安门广场较远,相信那里的路旁会有许多民众,王维林到了路旁,可以迅速没入人群,安全离开。
他努力使用控制器,不断地倒带停带,终于看清了坦克侧面的编号,知道这些坦克属于天津警备区坦克1师。
如果上述人类学教授的研究结果和判断,基本可以断定,王维林凶多吉少,可能已经在戒严
部队军人的暴力下遇难。天安门广场清场前后在广场内外被捕的学生和民众都遭到军人的暴打,用木棒,用枪托,打死不少人,受伤致残的更多。山西的大学生高旭
在广场被捕,被打伤致残,他叙述了具体的经历。被捕者都关押在天安门城楼左右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里,那里成了军人泄愤的大刑场。被捕者三天没有吃
喝。
[size=12]以后如果有一个人说他是王维林,可能大家都很难相信。‘六四’实际上最后成为一个宗教
性事件,每年‘六四’对死者的纪念,已经成为一个宗教仪式。我们都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去悼念死者,而王维林成为一个‘神话’。王维林作为“六四”的象征,永
远活着。王维林和许多“六四”英雄一样,已经遇难。

丁子霖所搜寻的「六四受难者名册」中,这些名字仍然像黑色纪念碑一样沉重:
六部口才是真正坦克辗人的地方
节录自
高新《六三之夜:谁开枪?》
我
们在天安门万余名大学生和市民群众面临生命危险,同时也不愿由于天安门的抵抗给士兵造成生命损失的时候,理智地选择了妥协与和平,包围天安门广场的部队在
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和平主张的前提下应该说表现的是比较理智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负责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的部队主要不是从西线开枪打进来、已经失去理
智的部队,而是从人民大会堂等处出来的。没有遭到过抵抗的部队当然也就没有开过枪的部队。但是,长安街上的戒严部队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和平主张而全部理智起
来。当从天安门广场撤出来的大学生和市民陆续到达六部口地区时,一些惨无人道的士兵竟开枪扫射并驾着坦克冲向最多向它们扔了几块石头的人群。我和程真、沙
涛因最后撤离,所以幸免在六部口遭难。当我们三人手拉手步行到六部口以南的音乐堂时,一群刚被打回来的市民劝我们﹕“学生,再不能往前走了,前面的大兵一见你们这样打扮的就开枪。”我让程真和沙涛摘下头上的写有“绝食”字样的布条,我摘下胸前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徽,三个人还是硬着头皮朝六部口走去。
到达时,我们正好见到最后两具尸体被抬上一辆北京一三○卡
车。这辆车是被我和程真在前门箭楼东侧劝住运伤员的。当时,这辆车打着一面白底红十字旗对着驶近的坦克朝天安门广场里面冲,我们劝阻时程真险些被辗在车轮
下面。六部口的群众告诉我们,在我们到达这里之前已经运走了一批尸体,连坦克辗加机枪扫一共死了十三个人。事后有目击者告诉我是十一个人。横穿过长安街
后,我和程真、沙涛坐在六部口十字路口的西北角休息。最近的一辆坦克离我们不足两米,但这时它们已不再杀人了。也可能我们不骂它们法西斯的缘故。
从监狱里出来后我了解到,六部口遭难的十余人里,尚有一个坦克履带下的幸存者。他是北京某公司的职员,六月四号早上他听到中共开枪镇压的消息从家里出来,刚到六部口就遇上了撤出的学生队伍。他告诉我﹕“当时坦克驶近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朝人群里辗,所以也没有赶紧躲避的思想准备。从坦克开到我脸前的那一刻,我就甚么也不知道了。三天以后,我在医院里醒过来,医生都不敢看我。”他的右胳膊从肩膀处永远没有了,身上落下七十六处伤。刚被坦克碾过后头皮和一只耳朵被撕开,惨不忍睹。他在住院治疗期间,一位“同情者”诱骗后又拋弃了他的未婚妻,这个可怜的姑娘因为深感负疚和愧悔而自尽身亡。临死前留下遗书,请求他的宽恕并希望他能为自己料理后事。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坦克履带下的唯一幸存者时,正好是他刚从原来未婚妻的追悼会上回来。
写到这里,我想再补一句题外话﹕国内的假肢厂工人能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潜入工厂为这位坦克履带下的幸存者免费制作假肢,逃出国的一些“天安门勇士”(当然不是全部)在挥霍捐款时想到过“六四”的死难者和尚留在国内的受难者吗﹖不要忘了,当时,许许多多的大学生和北京市民都是受了我们的宣传上街,为了保护我们在天安门坚持民主斗争的大学生们才去堵截军车,才饮弹身亡或留下终生残疾的。
 (左)坦克压扁了一辆电单车(右)一名体育学院的学生 ,被坦克辗断了双腿的情况
(左)坦克压扁了一辆电单车(右)一名体育学院的学生 ,被坦克辗断了双腿的情况


| 吕鹏; 9 岁。小学生。被戒严部队射中胸部,当场死亡。 |
| 蒋捷连; 17岁。中学生。独子。在木樨地中弹穿胸而死。 |
| 叶伟航; 19岁。中学生。海军总医院第一号无名尸,右肩右胸及后脑中弹身亡。 |
| 萧杰;19岁。大学生。独子。逾红色警戒线,戒严部队喝令未从,子弹穿胸而死。 |
| 董晓军;19岁。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中,排尾被坦克压死,尸体碾碎。 |
| 王培文; 21岁。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中,排头被坦克轧死,尸体轧碎。 |
| 钟庆; 21岁。大学生。头部中弹,打掉半个脸,从衣袋钥匙才能辨明身分。 |
| 钱辉; 21岁。大学生。被坦克击破膀胱及大腿动脉,还说「当心!」血流一百米而死。 |
| 吴国锋; 22岁。大学生。独子。四川某偏远县分唯一的大学生。死后火化,父母领回骨灰。 |
| 田道民; 22岁。大学生。家境贫寒。做完毕业论文被坦克碾死。同学每年各捐十元给其父母。 |
| 何洁; 22岁。研究生。公认为神童,十五岁入清华大学,头部中弹亡。 |
| 刘弘; 24岁。大学生。腹部中弹,肠子流出,被同学塞回,死于同学怀中。 |
| 刘景华; 30岁。工人。夫妇均中弹,孩子送老家抚养。 |
| 宋晓明; 32岁。工人。军车子弹穿透大腿动脉,持枪军人命令不准抢救及输血而亡。 |
| 周永齐; 32岁。工人。子弹从左侧胸射入右肺穿出而亡,遇难时妻刚分娩15天。 |
由
1989年至1999年期间,
丁子霖教授共收集了受难者者共155人,
按此参阅按此进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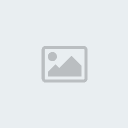
 首頁
首頁
 》》》》》》》
》》》》》》》






